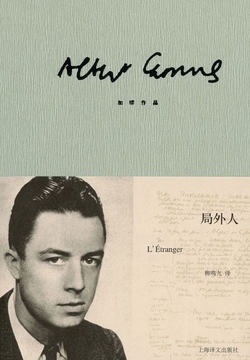作者: 【法】加缪 简介: 本小说塑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荒谬的人”——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的主人公默而索,他对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他母亲的去世,甚至自己被判处死刑,他都没有感觉…… 类型: 精品小说-社会小说
##摘抄
###四
-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爱不爱她。我对她说,这种话毫无意义,但我似乎觉得并不爱。
###五
- 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跟她结婚。我说结不结婚都行,如果她要,我们就结。她又问我是否爱她,我像上次那样回答了她,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可以肯定我并不爱她。“那你为什么要娶我?”她反问。我给她解释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希望结婚,那我们就结。再说,是她要跟我结婚的,我不过说了一声同意。她认为结婚是件大事,我回答说:“不。”
###六
- 稍过了一会儿,我转身向海滩走去。
- 我觉得天门大开,天火倾泻而下。我全身紧绷,手里紧握着那把枪。扳机扣动了,我手触光滑的枪托,那一瞬间,猛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切从这时开始了。我把汗水与阳光全都抖掉了。我意识到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在这种平衡与寂静中,我原本是幸福自在的。接着,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没有显露出什么,这就像我在苦难之门上急促地叩了四下。
###一
- 而我呢,这么一个老故事又重复来重复去,真叫我烦透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
- 但他打断了我,挺直了身子,又一次对我进行说教,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说不相信,他愤怒地坐下。他反驳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信仰上帝,甚至那些背叛了上帝的人也信仰。这就是他的信念,如果他对此也持怀疑态度的话,那么他的生活也就失去意义了。他嚷道:“您难道要使我的生活失去意义吗?”在我看来,这是他自己的事,与我无关。
###三
- 我的律师已经按捺不住,他举起胳臂,法袍的袖子因此滑落下来,露出里面上了浆的衬衣的褶痕,他大声嚷道:“说到底,究竟是在控告他埋了母亲,还是在控告他杀了一个人?”
###四
- 觉得我的律师的辩护词大概会讲个没完没了。有一阵子,我是注意听了,因为他这样说:“的确,我杀了人。”接着,他继续用这种语气讲下去,每次谈到我这个被告时,他都自称为“我”。我很奇怪,就弯下身子去问法警这是为什么,法警要我别出声,过了一会儿,他说:“所有的律师都用这个法子。”我呢,我认为这仍然是把我这个人排斥出审判过程,把我化成一个零,又以某种方式,由他取代了我。
- 由于这些长篇大论,由于人们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没完没了地评论我的灵魂,我似乎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一片无颜无色的水,在它面前我感到晕头转向。
- 铃声又一次响起,门开了,我一出现,大厅里就鸦雀无声,真是一片死寂,我看见那个年轻的新闻记者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我突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
- 没有朝玛丽那边看。我已经没有时间去看了,因为庭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向我宣布,将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
###五
- 他把眼光移开,身子仍然未动,问我这么说话是否因为极度绝望。我向他解释说我并不绝望,我只不过是害怕,这很自然。他说:“那么,上帝会帮助您的。我所见过的处境与您相同的人最后都皈依了上帝。”我回答说,我承认这是那些人的权利,这恰恰说明他们还有时间这么做。至于我,我不愿意人家来帮助我,而且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兴趣的事情再产生兴趣。
- 神甫朝他周围看了看。我突然发现他答话的声音已变得疲惫不堪了,他说:“所有这些石块都流露出痛苦,这我知道。我没有一次看它们心里不充满忧伤。但是,说句心里话,我知道,你们这些囚犯中身世最悲惨的,都从这些黑乎乎的石块上看见过有一张神圣的面孔浮现出来。我们要求您看的,就是这张面孔。” 我有点激愤起来。我说我每天瞧着这些石壁已经有好些个月了,对于它们,我比世界上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更为熟悉。也许,曾经有好久的时间,我的确想从那上面看见一张面孔,但那是一张充满了阳光色彩与欲望光焰的面孔,那就是玛丽的面孔。我白费了力气。现在,彻底完了。反正,从这些潮湿渗水的石块里,我没有看见浮现出什么东西。
- 背对着我站了好久。他待在这里使我感到压抑,惹我恼火。我正要请他离开,不要再管我,他却转身向我,突然大声叫嚷了起来:“不,我不信您的话,我确信您曾经盼望过另外一种生活。”我回答说那是当然的,但那并不比盼望发财、盼望游泳游得更快,或者盼望自己长一张更好看的嘴巴来得更为重要。这都是一回事。他打断我的话,他想知道我是如何设想另一种生活的。于是,我朝他嚷了起来:“就是那种我可以回忆现在这种生活的生活。”立刻,我又对他说,我已经受够了。他还想跟我谈上帝,但我朝他逼近,试图最后一次向他说明我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不想浪费时间去跟上帝在一起。他企图变换话题,问我为什么称他为“先生”而不是“我的父亲”,这可把我惹火了,我对他说他本来就不是我的父亲,他到别人那里去当父亲吧。
- 这时,不知是为什么,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东西爆裂开来,我扯着嗓子直嚷,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抓住他长袍的领子,把我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猛地一股脑儿倾倒在他头上。他的神气不是那么确信有把握吗?但他的确信不值女人的一根头发,他甚至连自己是否活着都没有把握,因为他干脆就像行尸走肉。而我,我好像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但我对自己很有把握,对我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比他有把握得多,对我的生命,对我即将来到的死亡,都有把握。是的,我只有这份把握,但至少我掌握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以前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永远有理。我以这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我干过这,没有干过那,我做过这样的事,而没有做过那样的事。
- 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是有重要性的,我很明白是为什么。他也知道是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整个那段荒诞生活期间,一种阴暗的气息从我未来前途的深处向我扑面而来,它穿越了尚未来到的岁月,所到之处,使人们曾经向我建议的所有一切彼此之间不再有高下优劣的差别了,未来的生活也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切实在。其他人的死,母亲的爱,对我有什么重要?既然注定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的生活幸运儿都像他这位神甫一样跟我称兄道弟,那么他们所选择的生活,他们所确定的命运,他们所尊奉的上帝,对我又有什么重要?他懂吗?大家都是幸运者,世界上只有幸运者。有朝一日,所有的其他人无一例外,都会判死刑,他自己也会被判死刑,幸免不了。
- 这么说来,被指控杀了人,只因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处决,这又有什么重要呢?沙拉玛诺的狗与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区别,那个自动机械式的小女人与马松所娶的那个巴黎女人或者希望嫁给我的玛丽,也都没有区别,个个有罪。雷蒙是不是我的同伙与塞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这有什么重要?今天,玛丽是不是又把自己的嘴唇送向另一个新默尔索,这有什么重要?他这个也被判了死刑的神甫,他懂吗?
- 从我未来死亡的深渊里,我喊出了这些话,喊得喘不过气来。
- 好像刚才这场怒火清除了我心里的痛苦,掏空了我的七情六欲一样,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